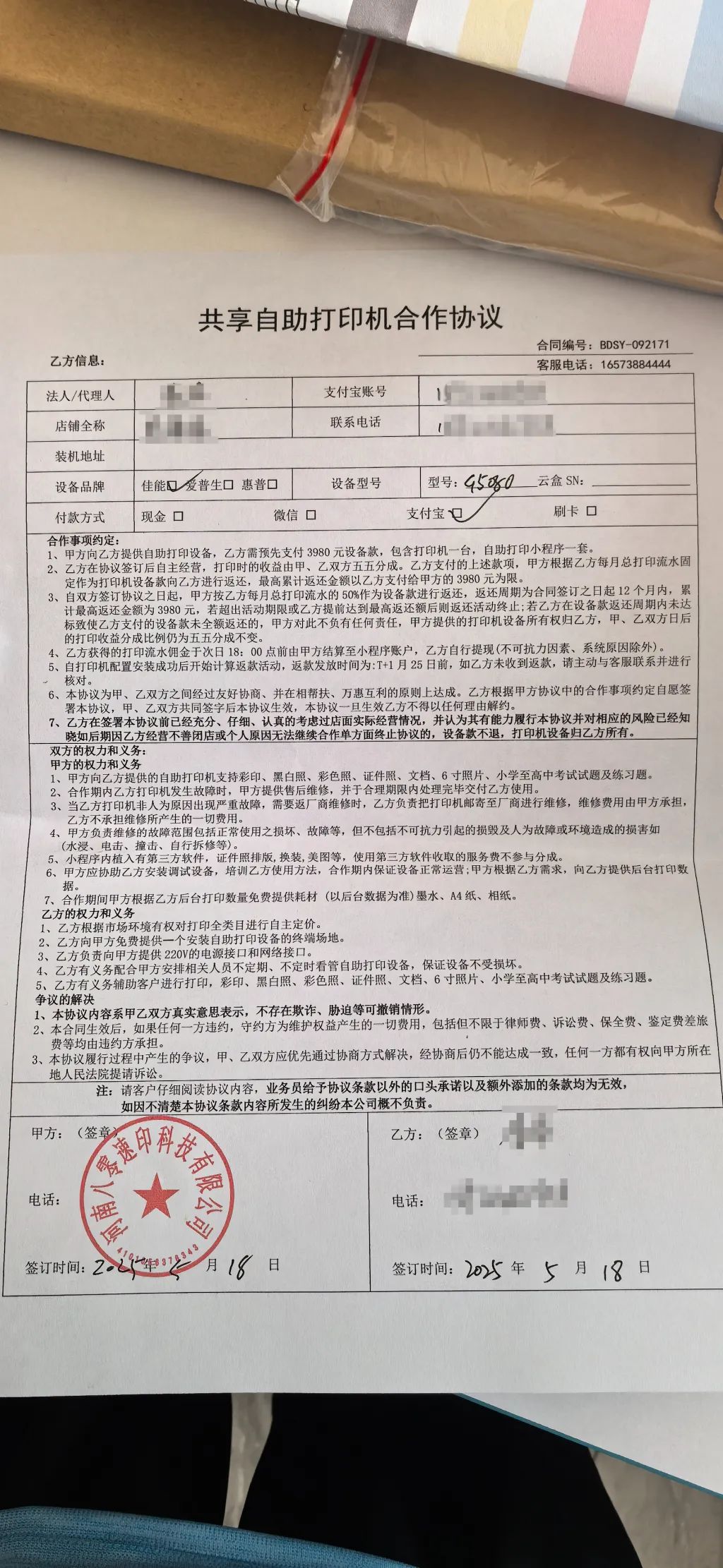【编者按】
2025年3月,中国已经对38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入境短期旅游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在上海亦生活着许多外国人,他们有的在此客居一段日子,也有的把这座城市当作了他们的家。对很多外国人来说,上海是他们了解中国的第一站。在新项目《上海之旅相册》中,澎湃新闻邀请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和上海产生交集的外国人,邀请TA们打开自己的手机或者相机,分享记录上海的照片与故事。
迈克·弗里曼(Michael Freeman)是一位英国摄影师,他1998年第一次来到上海,之后的近三十年里,他多次回到这座城市。“一开始,我也被外滩那令人震撼的美所吸引,但后来,我慢慢注意到了这里的日常生活、城市运转方式和人们在街头的互动景象。”弗里曼作为职业摄影师的兴趣点在于城市的街道,而在生活中,他喜爱这里的美食、公园、梧桐树,甚至是便利的公共卫生间。“我儿时受到摄影师恩斯特·哈斯的影响,他在1952年为《生活》杂志拍了一个专题,名为‘魔幻之城’。1950年代的纽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充满活力、最令人兴奋的城市。”弗里曼说,“但在70多年后,上海是今天的‘魔幻之城’,中文里很多人爱叫它‘魔都’。”
“手机比较便捷,我上街拍照几乎很少用相机。”弗里曼说。他分享了一些照片,这些并不被他称之为“作品”的照片既像他的生活记录,又隐约透露着他的视觉兴趣。过去五年,他担任苹果公司的影像美学顾问。“我研究手机照片看起来怎么样,这个问题有它的两面性,它极其方便,但它剥夺了人们在社会中互动,那种物理的、传统的正常的方式。正如你所见,我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因为我喜欢摄影本身。但我最大的满足感还是来自于我们称之为纪实报道摄影(documentary reportage)的东西,这本质上是关于人们在他们世界、环境和背景中的故事。”弗里曼说。

上海张园
以下为弗里曼自述
我是个职业摄影师,全职从事摄影工作已有50年了,我拍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纪实报道类,实际上,我最初是为杂志完成拍摄任务的,当时纸质杂志很受欢迎,会委托摄影师去各地拍摄。在那之后,我主要拍摄一些大型的专题,然后做成摄影画册。因此我需要大量旅行,也自然绕不开来到中国。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5年,来到上海则是1998年。那时是10月下旬,天气晴朗,令人心旷神怡,我立刻被这里迷住了,像游客一样直奔外滩,日出时外滩的景色美得令人震撼。作为一名摄影师,这往往是拍摄城市时的常态。先映入眼帘的是宏伟的景色,但后来,我不断回到这里,日常生活、城市的运转方式、以及人们如何在街头互动的景象成为我热爱拍摄的题材——这也是我认为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我在这座城市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一直专注拍摄些中国的主题,上海是我连接中国的基地,我已经拍了一本关于茶马古道的书和另一本名为《茶生活》(The Life of Tea)的书,今年9月,我也即将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个展。

我1998年来上海,那时我像游客一样直奔外滩,外滩的景色美得令人震撼。

上海展览中心的苏联式建筑。
我最近越来越多地在我住的街道附近拍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称之为“梧桐区”的地方。我和我中国朋友的圈子都聚集在这里,在永福路上一个叫融艺术的空间,我们喝茶、聊天、创作艺术和音乐。我是个来自伦敦市中心的城市居民,这里如此安静、绿树成荫、环境宜人,让我感到惊讶。我从未想过,在一个人口3000万的城市中心,我常常走出大门,却看不到路上有车行驶。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在朋友的艺术空间品茶。
我在上海喜欢拍的东西是普通人的生活人像。为此我现在通常用长焦镜头。我比较喜欢在街头艺术玩一些视觉戏法。日常的空间诱惑着艺术家去体验它们,这是错视画法 (trompe l'oeil) 的理念,西方的绘画传统早于街头艺术。在英语中,我们也使用经典的法语术语 Trompe l'oeil,意为“欺骗眼睛”。但在中国,“错视”的元素更新。所以在上海一个计划重新开发的城市街区,通常会用木板围起来,木板上画着画。

在上海一个计划重新开发的城市街区,通常会用木板围起来,木板上画着画。

我喜欢在照片里玩视错觉。

街头修补自行车轮胎的人。

街头的一位老太太。
我在上海没什么一成不变的日常,因为我是摄影师,每天永远不同,昨天、今天和明天总有不同的计划,我已经这样50年了,习惯每天做不同的事,我对此上瘾。
比起我1998年初次来的时候,上海更干净、更精致、也更有条理。它发展非常快。在上海任何购物中心走走都有很大的视觉刺激。我爱这里的很多东西:
比如美食,这里汇集了中国各大菜系,价格亲民,而且总能订到位子,在伦敦,订一家好餐厅可没那么简单。比如公园,这里遍布着种植精心的公园,甚至一个街角就有个小公园。比如徐汇区的梧桐树,绿荫蔽日,大城市下的林荫道是个享受,不过晚春我经常会因此打喷嚏,这是我要付出的代价。比如公共卫生间,这里的卫生间大多都挺干净的,伦敦在维多利亚时期设立了很多公共便利设施,但今天,很多厕所都上了锁被废弃了。还有英文标识,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英文标识,但在西方,你肯定找不到中文标识。
上海也有一点我不大喜欢:街上的狗屎。在英国,法律规定你必须捡起来,但这里人们有时不捡,我可不喜欢在街上看到它。

我去买包子,这是中国的日常早餐。

中国的美食大闸蟹。

早上的包子摊总是很忙碌,上午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人了,店员休息着玩手机。
我觉得上海是个“魔幻之城”(Magic City)。我讲一个不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摄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图片杂志之一《生活》杂志在1953年刊登了一个摄影专题,叫“魔幻之城”。他们把头版交给了奥地利摄影师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哈斯拍了1950年代的纽约,因为纽约那时是世界上最充满活力、最令人兴奋的城市。哈斯发现了那些让城市变得迷人的视角、细节、倒影和光线。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这个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然而,时代已经变了。70多年后的今天,无疑上海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哈斯初到美国时是个外国人,我在中国时也是如此,虽然局外人没有特别理由成为更好的观察者,但我们的目光或许会被略有不同的主题和时刻所吸引。这就是我拍上海的动机,它是今天的“魔幻之城”,但中文里很多人爱叫它“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