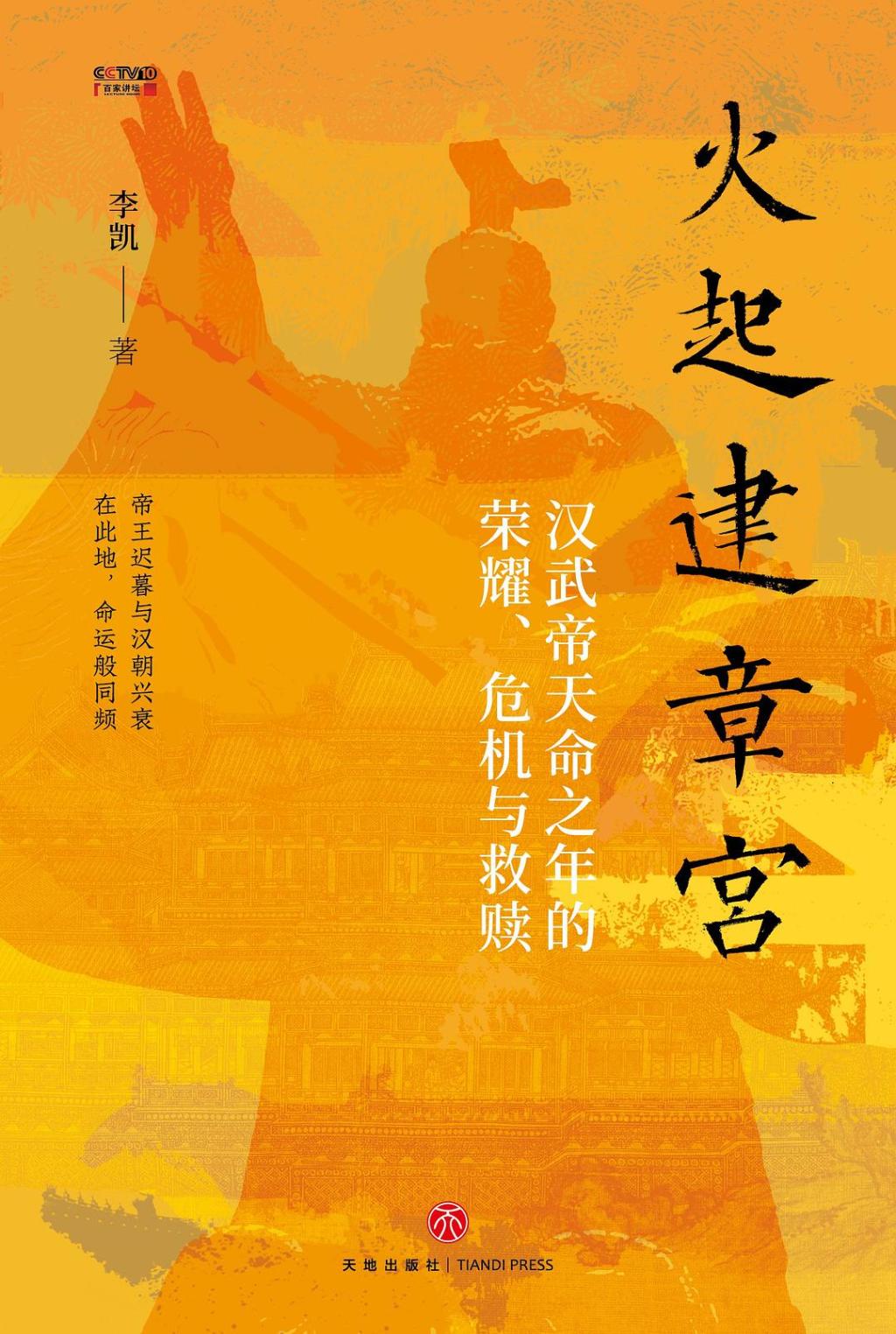说建章宫见证了汉武帝的荣光,并不过分。然而,汉昭帝刘弗陵对建章宫就没有其父的热情了。元凤二年(前79年),在执政数年后,汉昭帝从建章宫搬回未央宫,建章宫成了一般的离宫别苑,门可罗雀。地皇元年(20年),王莽索性拆建章宫诸殿之材以筑九庙,建章宫遂废毁。《汉书·王莽传》载,更始元年(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后曾火烧未央宫,“未央宫烧攻莽三日”,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这场兵燹有没有波及建章宫,还不确知。建章宫作为汉家重要的宫苑,自太初年间建造,其光彩和汉武帝中晚年的兴衰荣辱相始终。

汉武帝像,选自明代《三才图会》
《史记·六国年表》中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万物萌生于东方,成熟于西方。据此看来,开创事业的人必定出现在东南,收获果实的人常常出现在西北。以今天我们的知识结构看,古人认识到的规律还比较粗疏,带有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说色彩,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汉武帝平定闽越、东瓯、南越在东,经营西南夷、通西域在西;未央宫、长乐宫在东,建章宫在西。司马迁很大程度上似乎也没说错。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说的是人之常理。人们在年轻的时候从事的事情比较简单,势必要把硬骨头搁置一下;等时间久了不少难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此时已经不是少年。
汉武帝的中晚年,有着一系列成就。汉武帝不可能事必躬亲掌控王朝的一切,但他成功地驾驭了整个国家机器。这仰仗于秦统一以后的官僚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官员严格地囊括在中央集权的统辖之内。被官僚组织支撑起来的君主,在具体琐碎的生产生活事务上投入精力的可能性比较小;一层层的官僚替代君主从事与督察这些琐事,君主关心的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与秩序维护。汉代的制度较为健全,尤其是汉武帝颁行推恩令、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严禁诸侯王参政、裁抑相权、依靠亲信近臣参与决策、形成中外朝制、设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郡国的控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创举。《韩非子·扬权》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意思是君主应保持本色,抓住要害,不着形迹。政事在地方,要害在中央。圣明君主执掌着要害,四方臣民都会来效劳。《汉书·公孙弘传》载:
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弘不得一”颜师古注曰:“言其利害十条,弘无以应之。”老谋深算的公孙弘恐怕不是理屈词穷,而是看到了朱买臣背后是皇帝,故马上改口。法家主张权力不应表露无遗,不能轻而易举就亮出统治者的底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思路,不仅是法家的权术精神,也是大象无形的政治智慧。
汉武帝做的狂悖之事,很多都发生在他的中晚年。中晚年的汉武帝履行了以前的巡狩旧制,曾十次出巡,求仙求药为他的主要目的。元封元年(前110年,此时汉武帝过了不惑之年)“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已达天命之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禅”,“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太初三年(前102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上亲礼祠上帝”。
多次巡海,表明汉武帝留恋东海、笃信神仙传说。汉武帝欲封禅求仙之心极为迫切,方士公孙卿言黄帝封禅后就乘龙上天,汉武帝感叹:“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汉武帝居然无所顾恋至此。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秦始皇、汉武帝的巡狩行为已和以前明显不同。秦皇汉武不仅东上泰山,数至海上,而且遍祭五岳四渎,天下名山大川都有其车马痕迹。他们不仅基于儒家学者的巡狩构想,把受命改制、祭天告成、建立明堂、迷信谶纬灾祥的内容囊括其中,还有种种神仙方术的痕迹。秦皇汉武的巡狩,以谋求仙药而追求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于是各路方士、江湖骗子趁机迎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大肆作祟行骗。汉武帝比秦始皇更甚,“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武帝屡次上当,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假借求仙、丹砂炼金、入海寻药之名,骗取汉武帝的信任,谋取巨额钱财与爵位(《史记·封禅书》)。这样诸多学说杂糅在一起,巡狩封禅已经背离了“功至”“德洽”的精神,降格到神仙方术、鬼神之事的层面,与现实政治需要严重脱节了。
汉武帝此时的巡狩行为谈不上是早期国家时代尧舜禹那种勤政为民之举,也没有秦始皇务实,更多地停留在皇权炫耀的层面上,甚至成了典型的劳民伤财、穷奢极欲的行为。故后代帝王若非有特殊需求,几乎不动巡狩这个念想。帝王如有巡狩之念,大臣多予以规劝,以避免重蹈秦皇汉武劳民伤财的覆辙。
秦汉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大一统之所以出现在这一时期,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牛耕的使用得到广泛推广,旧有的上层建筑逐渐瓦解,被史家称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群人在历史舞台上异军突起。他们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与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顺应君主集权的趋势,支持并巩固统一,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商鞅、李斯、秦始皇、汉武帝这些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用武力和行政手段维系社会秩序。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集权与统一终于在秦汉得以实现。尤其是郡县制的确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就东周秦汉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层建筑的调整等方面予以详细而全面的论述。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汉武帝无疑是个焦点。汉武帝强化集权的种种行为,虽然致使民怨沸腾,但王朝没有土崩瓦解,疆域版图、行政制度等一系列政治资源被后继者承袭下来,在他的儿子、曾孙统治时期出现了富庶繁荣的昭宣中兴。这是汉武帝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幸事。汉武帝被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仁义”不过是他帝业的装点,未必称得上成功;但“多欲”的确是事实,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中老年阶段。
对汉武帝,汲黯说“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大体是不错的。汉武帝给人们的印象是滥用权力,手段严苛。宋朝学者洪迈写的《容斋随笔》,说汉武帝“忍而好杀”,这和他标榜的圣人经术大相背离。上行下效,当时官场上酷吏横行,大名鼎鼎的杜周面对他人的指责就曾经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按照常理,法令有常为好,因为这样老百姓就懂得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天下才能大治。可是汉武帝非常专断,以君主的个人意志践踏朝廷章程,十几位丞相中多数不得善终,大臣无罪被杀者甚众,受株连的不计其数。
在高压政策下,百姓性命如同蝼蚁,社会矛盾多,民变也频繁,人们对汉武帝的非议很多。司马迁本要继承父亲遗志,讴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但他记录下的绝非繁花似锦的太平天下,而是一片危机四伏的景象。明代人钟惺的《钟伯敬评史记》言,《史记·封禅书》妙在“将秦、汉以来坛畤祀典与封禅牵合为一,将封禅与神仙牵合为一,又将河决、匈奴诸事与求仙牵合为一,似涉傅会,而其中格格不相蒙处,读之自见;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䄠,绍周后”的汉武帝,做出许多背离天意人心之事,令后世大跌眼镜。此外他还很迷信,想长生无极、超越生死,但现实无情地摆在他面前。
汉武帝周围像少翁、李少君、栾大一类的江湖骗子就很多。或许,若不是汉武帝迷信鬼神巫术,也不会对巫蛊之事如此震怒并酿成大难。为什么绝顶聪明的帝王会在这一点上犯糊涂?其实道理也不难懂,削封国、打匈奴、通西域、罢黜百家、盐铁官营在汉武帝眼中,是能够凭借他的思维进行布局的,但是这一切能否完成,要看上天是否给他足够的时间。
清朝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就说东汉的皇帝多不长寿,所以大权旁落、政局动荡:
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惟献帝禅位后,至魏明帝青龙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诸帝之年寿也。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
汉武帝的成功,与其掌握王朝最高权力五十多年不无关系。东汉皇帝在成功之前天不假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汉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术士新垣平官至上大夫,曾经让人献玉杯,刻有“人主延寿”四字。汉文帝高兴极了,因而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天下欢乐大饮酒)。后来大臣张释之等人上书皇帝,奏明新垣平所言皆诈,他的玉杯是哪里伪造的都被查了出来。汉文帝勃然大怒,下吏治罪,新垣平被灭三族。汉代帝王中的楷模汉文帝都会被诓惑,可见帝王心中多么渴望长生。
建章宫始建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是长安城西一处大规模的宫室,有着延续长安原政治中心未央宫的特殊意味,绝非普通离宫别苑。营造建章宫时,汉武帝已年逾五十、在位近四十年,权力达到极盛。十七年后,汉武帝寿满天年,没能实现他的长生之梦,却给大汉王朝乃至千秋万代留下了包括建章宫在内的诸多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丹药、神仙、建章宫和汉武帝的中老年相始终,令人深省。
建章宫的兴建,缘起于柏梁台的失火,让汉武帝有机会兴建一座更为豪华的宫殿。建章宫与汉武帝的交集仅有十七年,这十七年中,汉武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西汉也进入社会矛盾加速积累的时期。可以说,建章宫诞生于汉武帝人生的巅峰时期,也诞生于西汉王朝的辉煌时期。直至王莽时代,建章宫主体建筑被拆除,西汉也于此终结。建章宫兴起于大火,也最终消失于兵燹前后。悠悠千载,仿佛没有什么人和物能实现永恒。汉武帝和他钟爱的建章宫,在历史的火起火灭中一同缥缈远去,只剩裸露的台基和颓圮的墙体讲述着那段盛衰往事。

《汉宫春晓图》(局部),明代仇英绘
20世纪70年代末,甘肃嘉峪关以西约100千米处的玉门花海汉长城烽燧里出土了一批汉代简牍。其中一枚汉代的七棱觚尤为珍贵,上面书写的竟然是汉武帝的遗诏。觚是汉代简牍的一种,一根木棍削成多面,增加了书写的空间。这枚木觚抄写年代是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左右。上书文字大致如下:
制诏皇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祠,加增朕在,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听谏士。尧舜奉死,自致天子。胡亥自恣,灭名绝纪。审察朕言,终身毋疚。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惕惕,恐见故主。毋责天地,更亡更在。太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忌。
从中可以看出,汉武帝临终时看淡死生,展现出他仁慈通达的一面,和先前执着于求仙、热衷于杀伐的形象判若两人。这份遗诏竟然出现在远在边疆的烽燧里,足以说明汉代皇权影响之深。经研究,这是汉代边陲戍卒“学书”之物,那么其中就应当带有人们对这份遗诏即对于汉武帝晚年思想转变的认同感,即便它是官样文章。换言之,它流露出来饱经涂炭的民众对于“文景之治”那种太平盛世的回忆和向往。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汉武帝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永恒,可这种永恒并不是靠神仙方术得来的。不是他的寿命永恒,而是他的思想、事业为后人所继承。汉武帝求仙问药,没长生不死;他耗费资材营造的琼楼玉宇,也早已灰飞烟灭;反而是经历一系列变故和挑战的汉家的制度、思想和治理国家的智慧,成了千秋万代的文化遗产。
(本文选摘自《火起建章宫:汉武帝天命之年的荣耀、危机与救赎》,李凯著,天地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